形式婚姻(Marriage Of Convenience),简称形婚,“形式婚姻”原本是指某些人为了实现某种以已婚为前提条件的特定目的而与他人假意结婚以取得已婚身份,即婚姻只是达成某种特定目的的工具或手段,其目的包括利益共享、政治联姻等形式,而无实质内容。

形式婚姻主要分为异性恋形式婚姻和同性恋形式婚姻。形式婚姻是人们迫于传统的家庭观念和社会主流趋势而选择的一种满足社会期望与保护自己的工具,其常见的表现形式有“领证”“居住在一起”等。形式婚姻也是一种在男同性恋者和女同性恋者之间的互助婚姻模式,“夫妻”双方在生理和人格上都保持独立,只是借助婚姻的形式抵挡外界的压力,与此同时,他们可能各自保持自己的同性恋爱关系。其中,承担家庭责任、争取个人自由和获得现实利益是同性恋者进入形式婚姻的主要动力,形式婚姻可能缓解社会和家庭催促同性恋者结婚的压力。
形式婚姻的出现会对传统婚姻制度造成冲击。选择形式婚姻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心理压力,进而造成情绪低落;以及婚后因为是否生育孩子双方彼此意见不合,在经济、家务、个人生活上也会出现分歧,并存在面对一些法律风险。
形式婚姻(简称形婚),指的是只有表面形式而无实质内容的婚姻,或在男同性恋者和女同性恋者间的互助婚姻模式。其主要分为异性恋形式婚姻和同性恋形式婚姻。其中,异性恋形式婚姻是指某些人为了实现某些以已婚为前提条件的特定目标(如求职、升迁、买房、办移民、减缓社会压力等)而与另一人通过婚礼或法律上的结婚手续取得已婚身份,而实际上,夫妻双方在身体和人格上都保持独立。而同性恋形式婚姻只是借助婚姻的形式满足家人和社会对其成员缔结异性婚姻的期待,与此同时,他们可能各自保持自己的同性恋爱关系。即婚姻只是达成某种特定目的的工具。
在20世界90年代末,中国开始出现形式婚姻。最早提出“形式婚姻”这个概念的是南京的金先生。金先生是一名同性恋者,1999年从国外回来的时候,面对家人催促结婚的要求,请求张北川教授根据外国同志圈中流行的男女结伴情况在其编辑的《朋友通信》上发布了一条消息,希望由此寻求适当条件的女同性恋者结成形式婚姻家庭关系。这种形式婚姻又称互助婚姻,是指男同性恋者和女同性恋者按照传统婚姻模式相结合。他们只需要去民政部门登记结婚,或举办一场民俗婚礼,不需要组建真正的家庭,没有实质性的家庭关系,没有共同财产,双方依然保持完整的自我,保持同志身份在人格和生理上的独立。

1997年,中国修改国家刑法后,将自愿的成人同性恋行为非刑罪化,2001年,卫生部将精神疾病清单中的同性恋行为删除。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其逐渐成为了同性恋者寻找“形婚”的温床。2005年,中国形式婚姻网成立,其目的为帮助同性恋人们寻找婚姻伴侣。截至2013年4月,该网站的注册用户有约16万人,至2014年9月,网站的注册用户已经达36万余人,次年10月,网站的注册用户已经达到了39万多人,其中近5万人寻“偶”成功。此外,匿名的QQ群、论坛也为同性恋者提供了交流机会。男女同性恋者为了完成家人赋予的传宗接代使命,或为掩人耳目,他们组成的“形式婚姻”家庭在圈子里渐渐成为了一种潮流,此现象也引起诸多媒体做专访报道。
随着社会发展,婚姻关系和婚姻形式等一直在发生着变化。人们为了避免传统婚姻观念家庭的压力去选择“形式婚姻”,既能完成父母亲戚的要求,也能获得自己需求。因此“形式婚姻”作为一条较为折中的方式,成为同性恋群体和其他类型的性少数群体的选择,在不违背社会传统观念的同时又希望自己可以有自由的恋爱关系,形式婚姻实质上是对中国传统婚姻观念的一种冲击。一些青年同性恋者不愿意重蹈几代同性恋群体步入同直婚的悲剧,而更加青睐于兴起的、由男同性恋者和女同性恋者通过合法婚姻组成家庭的形式婚姻。满足原生家庭的期待是同性恋者进入形式婚姻相当重要的原因之一,当男女同志把完成家庭责任当成是最重要的愿望的时候,他们更加容易向传统家庭制的意识形态妥协。
除同性恋者本人具有结婚压力外,同性恋者的父母也会遇到子女不婚为他们带来的困扰。部分父母在子女公开性倾向后依然希望子女进入异性婚姻,从而选择支持子女进入形式婚姻。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基础是家庭和宗法,也就是先有家族观念,再有人道观念。为了保证推动从家庭到宗嗣再到社稷环环相扣的伦理体制的正常运转,结婚及婚内生殖成为超神圣的性义务。在这种社会文化背景下,同性恋者父母面临的困难不仅是接受作为同性恋者的子女,还有如何面对亲戚、邻居。在强制异性婚姻的社会环境下,部分男女同性恋者不愿意重复前几代同性恋者与异性恋者步入婚姻的悲剧,而选择了在同性恋社群内寻找异性与自己进行合作,以完成社会和家庭的期待。
中国有许多为了获取公共政策带来的利益,或是规避公共政策造成的不利而为的形式婚姻。许多同性恋者出于获取现实利益的考量选择形式婚姻。在许多工作场景中,已婚人士更易受到提携,而工作中的社交场合,已婚身份背后的家庭责任感和家庭生活相关的话题也更易拉近职场中的人际关系。所以已婚的社会地位能够使他们得到同辈和长辈的认可。也有一部分理想主义者对婚姻充满了憧憬和想象,认为婚姻是一个具有吸引力的、可以带来稳定生活的机制。在无法与同性伴侣缔结婚姻关系的情况下,希望借由形式婚姻的方式获得稳定。

在中国实行夫妻共同财产制的背景下,因为形式婚姻在法律意义上被认定为真实有效的婚姻,所以在没有协议约定的情况下,离婚时双方婚后共同财产进行分割就会按照《民法典》中规定依法进行分割。如果没有婚前或者婚内协议,婚变后很容易发生纠纷。形式婚姻人士在婚前可以将双方的财产状况进行梳理并约定归属和分配原则。婚前财产协议是对夫妻婚前个人财产、婚后共同财产的分配的协议。该形式的约定也是婚前协议中非常常见的内容,在婚前将夫妻双方的个人财产、婚后共同财产的归属问题理清。
按照我国民法典规定,男女双方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者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
生育权系公民的人身权,也是一种人格权。男女双方都具有生育权,但是,当形式婚姻中男女双方生育权冲突时,男方不得违背女方意愿主张其权利,即一方生育权利的实现不得妨碍另一方生育权利。在男方坚持要孩子而女方不愿生育的情况下,如果男方做主,就意味着丈夫享有对妻子身体和意志的强制权,这将以女性人身自由的丧失和身心摧残为代价。夫妻之间享有平等的生育权,不得以附加一定的经济条件作为约定。当两个平等的权利相冲突时,其行使必然有先后,无论从何种角度出发,都应当首先保护妇女的权益。
形式婚姻是法律意义上的合法夫妻,夫妻除了意味着婚姻关系,还意味着双方存在一定的监护、代理的法律身份。假如说形式婚姻中的一方发生意外必须马上签字进行手术,有权利签字的一般只能是配偶和父母、子女。如果不存在形式婚姻关系,可以按照民法中的“意定监护”条款设定监护人。

形式结婚又称假结婚、通谋虚伪的结婚,是指为了实现其他目的登记结婚,这种婚姻双方没有共同生活的意愿,并且附加条件或者期限,约定在目的达成以后,即行离婚。和其他共同生活的形式不同,婚姻是法律规定的伴侣关系,这意味着,婚姻一旦有效缔结,就依法产生相互的权利义务。比如夫妻财产关系、债务承担、家事代理权、子女抚养、继承以及夫妻之间的体谅义务等。因此各国都要求婚姻的缔结必须符合一定的形式要件,以产生公示效果,也是为了保护第三人的信赖利益。
2017年,中国政务舆情监测评论提出,当为了突破政策限制而获取灰色利益的“假结婚”成为一阵风气蔓延开来时,则需要反思与检讨的,就不仅仅是那部分“投机取巧”的人,反而是政策与制度本身了。虽然形式婚姻反应了一部分人婚姻观念“功利化”倾向和道德伦理的沦丧,但也必须反思政策设计是否科学严谨、防患未然,对于党政部门层面,要针对一些违纪者通过离婚对抗纪委审查,加大领导干部婚姻变动申报的必要性,加快建立健全虚假婚变识别防范及失信惩戒机制。
在婚姻自由原则下,中国婚姻法规定结婚,只要当事人达成合意,满足婚姻法规定的实质要件,并在民政部门注册登记后,就产生合法有效的婚姻关系。中国《民法典》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款是有关于通谋虚伪表示的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但不同学术观点对此的解释不同。目前主要有两种观点:“意思主义”和“表示主义”。
依“意思主义”的观点来看,为了尊重当事人内心的真实想法,通谋虚伪表示应当适用于虚假婚姻,即当事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婚姻行为认定无效。但是该无效也应当在对虚假婚姻所涉及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中加以区分。在通谋虚伪婚姻中,假结婚的双方当事人该观点虽然尊重了民法学意思自治的基本原理,从法律效力的角度保护了当事人的内心真实意思,但是该观点也直接损害了登记主义制度的公信力。

依“表示主义”的观点看来,虚假婚姻应当不适用通谋虚伪表示的规定。因为在中国,婚姻行为只要具备了合法有效的登记要件,即符合《婚姻登记条例》和民政部《婚姻登记工作暂行规范》的规定,且民政部工作人员也对该民事主体履行了合格的形式审查义务,那么就应当认定该行为合法有效,从而不再考虑登记主体是否以虚假的意思表示而实施婚姻行为。该观点以维护现有的婚姻登记制度为出发点,既保障了公示的效力也维护了社会秩序的安定。然而该观点也存在弊端,因为虚假婚姻的背后往往隐藏着特殊目的。当特殊目的侵害了国家、社会公共利益,违背了公序良俗,但却因为目的隐藏性而使其顺利实现,那么婚姻制度便丧失了其应有的价值沦为了当事人的工具。
社会学家李银河致力于推动同性婚姻合法化。从第一次提出在《婚姻法》中加入“同性婚姻”的条款起,随后几乎每年两会前夕,她都会委托关注此问题的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将这份草稿提交上去。但每次都石沉大海。建议中,李银河指出,“据统计,男女同性恋人口在人群中会占到3~4%,在中国就是3900万-5200万人。由于没有同性婚姻法,这些同性恋者大多数会同异性结婚生育。”这也是张北川一直担忧的“同妻”命运的根源所在。在张北川看来,“形婚”与“同妻”性质完全不同。只要不违背“自愿”和“无伤害”这两大原则。张北川把形婚形容为“一种夹缝里的反抗”。他说,“让社会真正接受同性恋是一个很缓慢的过程,形婚只是一种过渡。”
形式婚姻对于中国的同性恋群体而言并不是一个完美的选择。形婚的稳定性较差,可能诱发种种问题。比如伴侣双方如何划分经济责任和家务、是否育儿、如何选择辅助生殖技术时、如何承担育儿中的父母角色,以及养老、翁婿婆媳关系、经济纠纷问题,等等。因此,形婚双方需要通过协同方式,组成戈夫曼意义上的“剧班”。这要求形婚者通过对自我身份的隐藏和调整“合作式”地表演异性恋夫妻,从而隐藏自身潜在背负的同性恋“污名”,并完成家庭和社会责任。
也有一种声音认为人们不应当完全否定形式婚姻的作用,步入形式婚姻的人不能称为服从传统的妥协者,而是通过他们的具体婚姻实践和策略,积极地调解家庭、个人以及社会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并且采取策略扩展自己的生活空间,包括寻找适合自己的关系模式和生活方式。他们通过进入形式婚姻与对方结成盟友,建立一种新的关系模式,呈现了性少数社群更为多元复杂的现象。对于中国的同性恋群体而言,形婚成为一种看起来可以兼顾传统价值观和个人自主性的理想选择日。形婚能够照顾到父母和家庭的体面,满足父母对子女成婚的最低期望,保护父母不受到社会歧视。部分同性恋者还可以通过形婚获得一定的家庭经济资助。另外,由于形婚双方所形成的契约关系,他们往往在婚后仍旧会和自己的同性伴侣一起生活,因此能够保证婚姻中的男女双方拥有最大的自主权,使双方比较自由地追求同性恋爱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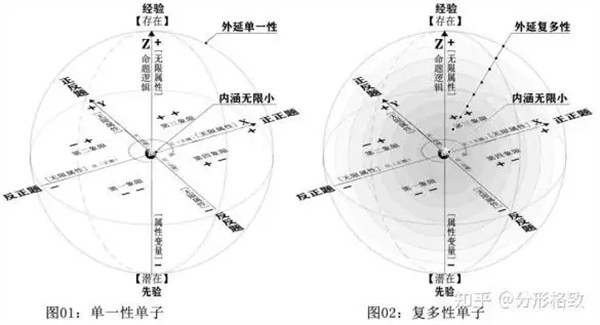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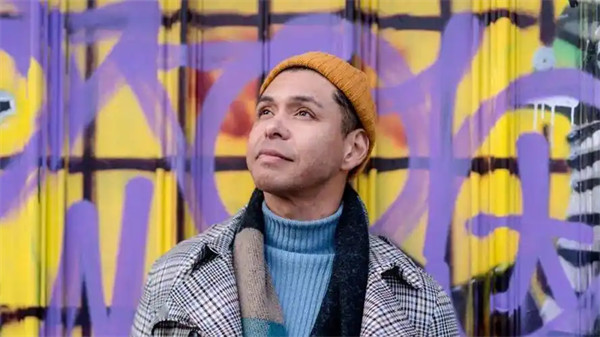




暂无评论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