吠陀时代(Vedic period,Vedio age)是古印度的一个历史阶段,开始于约公元前15世纪,终止于约公元前6世纪,因这一时期的史料主要见载于《吠陀》及解释吠陀的《梵书》《森林书》《奥义书》中,故被称作吠陀时代。在史料《梨俱吠陀》所反映的公元前1500-900年这一时期,被史学界称作“早期吠陀时代”。史料《梵书》《森林书》《奥义书》所反映的公元前900-600年或更晚的这段时间被称为“后期吠陀时代”。

古印度时代印度次大陆居住着如达罗毗茶人、摩亨殊达鲁人等组成的多个部落,分布于印度河流域。部分学者认为这一时代诞生的哈巴拉文化衰亡,是因为雅利安人的入侵,也有部分学者认为是自然灾害造成的结果。公元前1500年左右,雅利安人大规模进入印度次大陆,印度进入吠陀时代,但关于雅利安人是外来入侵还是形成于印度本土,学界一直存在争议。据《梨俱吠陀》记载,早期吠陀时代雅利安人与当地土著“达萨”及雅利安人内部常发生斗争。在交战中获胜的婆罗与普鲁人融合后形成了库鲁人。约公元前1000年雅利安人迁徙至恒河流域,开启了后吠陀时代。这一时期涌现出库鲁王国、潘查拉王国、维德哈王国等雅利安人与土著居民结合而产生的国家。后吠陀时期逐渐建立起的种姓制度使得这一时期阶级分化,战乱频繁。约公元前6世纪,波斯帝国皇帝大流士一世入侵印度,吠陀时代的结束。
吠陀时代的疆域北至雪山,西以苏莱曼山脉为界,东至沙罗室伐底河,往南延伸至海洋。在政治上,早期吠陀时代主要为氏族部落生活,存在“维达塔”“萨巴”和“萨米提”等议会组织,后吠陀时代随着种姓制度逐渐确立,形成了君主制和国家体制。宗教方面,早期吠陀时代以自然崇拜为主,并未发展为宗教,人们将各种自然现象神化、人格化作为其信仰的神灵;后吠陀时代在保留了原始宗教的多神崇拜的基础上出现了婆罗门教,与种姓制度相配合以规范人的行为。吠陀时代的社会经济以农业为主,大麦、小麦等为主要种植作物;畜牧业也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据一定地位;至后吠陀时代铁器工具出现,劳动分工加强,商业逐渐兴起。
吠陀文学是吠陀时代的重要文化,形成有《梨俱吠陀》《夜柔吠陀》《娑摩吠陀》和《阿闼婆吠陀》为四部重要本集,此外还有《梵书》《森林书》《奥义书》等由吠陀文学衍生出的一套文献体系。
“吠陀”意为智慧、知识,原是祭司在祭神时所用的颂歌、经文和咒语的汇编,主要为宗教内容,也包含部分雅利安人的早期历史。《梨俱吠陀》《娑摩吠陀》《夜柔吠陀》《阿闼婆吠陀》四部吠陀成书于公元前15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其中所记录的雅利安人大规模进入印度次大陆并在此发展的时期被称为“吠陀时代”。吠陀时代以四部吠陀成书的时间作为划分,《梨俱吠陀》所记载的公元前1500至前900年,称为“早期吠陀时代”“梨俱吠陀时代”;成书时期较晚的《沙摩吠陀》《夜柔吠陀》《阿闼婆吠陀》三本反映的公元前900至前600年,称为“后期吠陀时代”。
关于雅利安人是本土人还是外来人的争议主要围绕两个理论展开:雅利安人入侵理论(AIT)和印度之外理论(OIT)[a]。AIT认为,雅利安人在古代从印度外部,特别是从中亚地区入侵印度,带来了印欧语系和吠陀文化。这一理论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得到了广泛的支持,主要基于语言学、考古学和文献学的证据。19世纪的语言学研究揭示出早期雅利安人的语言——吠陀语,与希腊语和拉丁语在结构和发音上存在密切联系。随后,人种学研究和考古发现进一步印证了原始印-欧人共同起源的假设,他们可能起源于里海地区和南俄大草原,之后分散到欧亚大陆各地。其中,有一支在伊朗逗留了相当长时间,因此吠陀语与伊朗语族存在相似之处。大约在公元前1500年,这些原始印-欧人的一支通过兴都库什山脉进入印度西北部。此外,1907年在小亚细亚发现的赫悌石碑提供了额外证据,显示赫悌与雅利安人的祖先有共同的神祇。“雅利安”一词最初是一种语言的名称,后来误被用作民族的称谓,并且应仅限于指代向伊朗-印度迁徙的那一族。
然而,这一理论也受到了质疑,因为缺乏直接的考古证据来证明雅利安人的入侵。相比之下,OIT主张印度文化的本土起源,认为雅利安人并没有从外部入侵,而是在印度本土与其他族群混合和发展。这一理论的支持者指出,印度河文明和吠陀文化之间存在连续性,而且印度本土的考古发现也表明,印度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和多样性。此外,一些学者还从语言学和遗传学等角度提出了支持OIT的证据。然而,关于雅利安人是本土人还是外来人的争议仍然存在。一些学者认为,AIT和OIT并不是互斥的,而是可以相互补充的。也就是说,雅利安人可能既有外来成分,也有本土成分。此外,由于历史时期的复杂性和文献记载的缺失,很难确定雅利安人的确切起源和迁徙路线。
古印度时代印度次大陆居住着多个种族,如达罗毗茶人、摩亨殊达鲁人等在印度河流域形成部落,诞生了印度河流域文化,又称哈拉巴文化。哈巴拉文化衰亡的原因说法不一:诸多学者以在摩亨佐·达罗发现的骸骨为依据认为,是雅利安人的入侵造成了哈巴拉文化衰亡;也有部分学者如贾恩认为哈巴拉文化衰亡是洪水泛滥等自然灾害造成的结果。部分哈巴拉文化与雅利安人带来的吠陀文化结合,成为了印度文明的基础。公元前1500年左右,雅利安人大规模进入印度次大陆,居住于印度河河谷处,印度历史进入吠陀时代。雅利安人将印度河谷地区的土著居民称为“达萨”或“达休”,意为黑皮肤、没鼻子或鼻子扁平、说着邪恶言语的人种,与雅利安人在外表上有显著的区别。《梨俱吠陀》中记载了雅利安人因占领达萨的城镇与农业地区而与达萨的冲突,并将达萨描述为不祭祀、不遵守众神戒律的人。雅利安人初入次大陆以畜牧为生,后定居学农耕,种植大麦,牛马成为重要财产和交换媒介。他们初到印度时仍过着氏族部落生活,村落称为“哥罗摩”,由父权制家庭组成,有各种会议如“维达塔”、“萨巴”和“萨米提”等。

战争是这个时代的主要特点。雅利安人与“达萨”之间频繁交战,后来各部落间也为争夺财富和地盘而战,战争规模逐渐扩大。《梨俱吠陀》中还记载了雅利安人部落间的军事冲突。其中“十王之战”是早期吠陀时代最著名的战役。十王之战第一阶段发生于帕鲁什尼河(现代拉维)河畔,据《梨俱吠陀》记载十王之战中,一方为被称为Sudas Paijavana和Vasistha的婆罗多国王与其祭司,是雅利安部落的一支;其对手的名称不详,但应当包括普鲁斯(婆罗多的前主部落)、亚都(由图尔瓦萨指挥)、雅克苏、马特西亚斯、德鲁尤斯、帕克萨斯、巴拉纳斯、阿利纳斯、维沙宁、锡瓦斯、瓦卡纳和阿努。在这一阶段的战斗中婆罗多国王通过打开堤坝淹死了大量敌人,而奠定了战争的胜利。第二阶段战争转移至亚穆纳河岸边,当地部落比达与阿贾斯、希格拉斯和雅库斯被婆罗多击败。十王之战使婆罗多占领了以萨拉斯瓦蒂河为中心的整个普鲁领土,完成了向东迁移的过程。战后,婆罗多人还与普鲁人合并为一个新的部落,即库鲁人。这些战争使得贵族财富增加,“罗阇”权势提升。随着贵族财富和权力的增长,原先平等的氏族社会出现裂痕,等级制度的瓦尔那制度(种姓制度)开始萌芽。国家的出现已成为必然趋势。
早期吠陀时代后期,雅利安部落自印度河上游迁徙至恒河地区,约公元前1000年左右迁至整个恒河流域,开始了后吠陀时代。这一时期雅利安人不断扩张,并和印度土著居民进行接触、结合。次大陆广泛使用铁器,推动了耕地面积的迅速扩大和农业的发展。农作物品种增多,手工业也蓬勃发展,出现了各种专业工匠。经济的发展使社会结构再次发生变化,促使了雅利安人与土著及内部部落间的财富和土地争夺,阶级分化加剧,奴隶阶层人数增多,除战俘奴隶外还出现了债务奴隶,“达萨”一词也变为奴隶之意。
后吠陀时代“瓦尔那”制度开始形成,即种姓制度。社会出现了四个阶层:第一阶层为婆罗门祭司,第二阶层为武士贵族,第三阶层为自由农民和商人,第四阶层是奴隶、劳工和工匠。早期吠陀时代,雅利安人信仰简单的自然崇拜,将自然现象视为神祇,献祭祈福,在后吠陀时代这种宗教发展成婆罗门教,崇拜梵天为宇宙创造者。婆罗门教义以梵天神性为中心,垄断精神世界,祭司僧侣成为人间最高等级。原先的氏族部落机构也逐渐转变为镇压民众的暴力机器,过去民主选举产生的部落首领“罗阇”也就逐渐演变成了世袭君主。早期吠陀时代的社会组织“萨巴”和“萨米提”仍存在,但作用变小。公元前9至前8世纪,恒河上游的居楼和般陀罗已过渡为国家;至公元前7世纪,大多数部落完成向国家的过渡。
库鲁王国是后吠陀时代最早形成的国家,是由多个部落组成的超级部落联盟;吠陀赞美诗中出现新的仪式Śrauta,以此对部落联盟进行管理。库鲁王国的的权力中心位于今库鲁克谢特拉地区,是公元前1200年至公元前800年吠陀时代的第一个政治中心,其首都为阿桑迪瓦特(即哈斯提纳普拉)。《阿闼[tà]婆吠陀》中称赞库鲁之王帕里克希特是一个“繁荣王国的伟大统治者”;其子Janamejaya也被晚期吠陀文本称为伟大的征服者。Janamejaya统治时期出现了新的宗教祭祀仪式“马祭”,即让一匹的马自由地在王国中漫游一年,马后跟随一队被选中的战士,他们所到之处的王国和酋长必须向这匹马所属的国王致敬或与之战斗。
库鲁王国在被被非吠陀的萨尔瓦部落击败后逐渐衰落,吠陀文化中心向东转移至恒河流域的潘查拉王国(约在公元前900年至公元前750年)。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7世纪,维德哈王国成为更远的东方政治中心。至公元前6世纪,吠陀时代的各个政治单位合并为Mahajanapadas的大王国,开始了城市化进程,商业和旅行得到发展。安迦是位于摩揭陀以东的小王国,处于吠陀文化版图的最东部。亚达瓦斯向南扩张至马图拉,建立了瓦察王国,纳尔默达河和德干西北部成为吠陀文化版图的南部边界。
吠陀时代的结束以语言、文化和政治变化为标志。公元前6世纪初,大流士一世入侵,波斯文明进入印度地区。印度东北部展开了宗教革命,对吠陀宗教中繁琐的仪式和流血的祭祀进行反对,出现了耆那教、佛教等与吠陀人生观相悖的宗教。此后吠陀语系逐渐由印欧语系取代。
吠陀时代的印度版图北至雪山,西以苏莱曼山脉为界,东至沙罗室伐底河,往南延伸至海洋。据《梨俱吠陀》记载,多次出现“五河”这一地名,即旁遮普地区,是吠陀时代雅利安人的活动范围中心。

早期吠陀时代雅利安人在印度仍然过着氏族部落生活,但氏族部落模式已开始逐渐解体。各部落下有多个村落,这些村落被称为“哥罗摩”,村长称为“哥罗摩尼”,各村落则由多个父权制的大家庭组成。氏族部落间组织有各种会议,包括“维达塔”“萨巴”和“萨米提”。“维达塔”是最古老的会议,在早期吠陀时代较为盛行;一般全体部落成员都要参加,主要内容包括分配战利品,军事、宗教祭祀管理以及选举祭祀。“萨巴”是部落长老会议,一般由部落中少数的上层分子,即长老组成。“萨米提”则是部落民众的会议,由部落全体成年男子组成。各种会议组织与军事首领“罗阇”构成了早期吠陀时代的军事民主制的主要权力机构。
早期吠陀时代社会关系中奴隶制也逐渐发展,奴隶主要来源于雅利安各部族之间的战俘,包括异族和本族,大量的奴隶奠定了后吠陀时代国家、种姓制度、婆罗门教的产生基础。
种姓在印度语言中称为“瓦尔那”,意为颜色、品质。种姓制度最早产生于雅利安人进入印度次大陆之初,当时只有“雅利安瓦尔那”和“达萨瓦尔那”两个等级;至早期吠陀时代末期,雅利安人内部分化出婆罗门、罗阁尼亚、和吠舍三个等级,达萨成为首陀罗。到了后吠陀时代,罗阁尼亚转化为刹帝利,由此确立了印度社会严格的地位、职业等级:僧侣阶级为婆罗门,武士阶级为刹帝利,一般平民大众为吠舍,首陀罗则是社会地位最低的、被征服的土著居民。其中前三个种姓都为雅利安族,是雅利安民族内部分化而成的,只有首陀罗为被征服的异族;各种姓间有严格的界限,不能通婚,不得一起饮食。为维护种姓制度下的特权,统治集团编造神话以加强种姓制度的合理性,并试图以神的旨意将其确定下来。此后这种种姓制度世代加强,束缚了生产力发展和阻碍了社会进步,对南亚社会生活产生了消极影响。
为维护种姓制度,奴隶主阶级制定了诸多法律,其中《摩奴法典》最为典型。相传《摩奴法典》是大神梵天之子摩奴为确定人间社会秩序、各种姓义务制定的法典。《摩奴法典》认为婆罗门是人世间一切的主宰;规定首陀罗要为其他其他种姓服劳役,婆罗门和刹帝利有权菠萝首陀罗的一切;其中制定了诸多残酷刑罚以镇压吠舍和首陀罗的反抗;对各个种姓的行为进行了详细规定。各种姓阶层中存在相关机构处理种姓内部事务,并监督其阶层的人遵守《摩奴法典》,若有违背则会被处罚,甚至开除出种姓成为贱民。
后吠陀时代,阶级矛盾逐渐发展,使军事民主制机构逐渐演变为国家制度。军事首领罗阖成为世袭君主,通过贵族、官吏辅佐对国家进行统治,并逐渐神圣化。君主制度随之出现,成为吠陀时代政治组织的主要体制,部分地方也存在共和政府的形式。君主一般为世袭,也有地方称是由人民选举而产生的。君主的职责为保护臣民、支持祭司进行祭司;其收入来源于臣民的献礼或被征服的部族进贡。君主是因需要而选出的,故而君主必须遵守法律、不可专行。这一时期国家的具体行程过程缺乏详细的史料记载,但可知最初形成的国家是以部落中某一中心城堡为基地建立的,其规模较小,又被称为城邦。至公元前6世纪恒河及印度河流域已有了二十几个城邦国家,包括犍陀罗、俱卢、迦尸、居萨罗等,印度也由此进入列国时代。
吠陀时代雅利安人的经济生活多零散记载于这一时期的吠陀文学中。
《梨俱吠陀》中记载证明雅利安人以农业为主,吠陀中有大量的对田园之神的崇拜和农事活动的赞歌。这一时期雅利安人氏族部落逐渐解体进入阶级社会,农业逐渐取代畜牧业称为主要生产部门,以大麦、小麦等为主要种植作物。

早期吠陀时代畜牧业仍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据一定地位,部分定居于旁遮普的雅利安人减少了游牧生活,但在赞歌中仍然有关于畜牧方面的神普善的称赞。也有部分人以畜牧业为生,饲养家畜是其主要收入来源,如马、羊、驴等。同时也存在打猎行为,其猎物多为狮子、野猪、水牛、羚羊、鸟类等。
吠陀文学中也有提及买卖成交、高利贷、流通货币、水路运输等内容。可知吠陀时代存在大船进行交通,但可能仅用于内河航行。国内已有广泛的商业贸易,以牛和金饰作为货币;是否有海上贸易尚不确定。后吠陀时代由于社会发展与铁器的推广,劳动分工加强,促进了交换行为的发展,商业逐渐兴起。商品交换时,出现了以物易物和付偿购物两种方式的高利贷。
《吠陀经》是雅利安人时代口口相传的古代记录,记录了雅利安人的战争、王朝兴衰、文化发展轨迹等内容。吠陀文学包括四类:本集、梵书、森林书和奥义书,后三者为吠陀文学衍生出的一套文献体系。
本集是圣歌、祷文、咒文、祝福、祭祀经文及连祷文的总集,由五个集录组成:《梨俱吠陀》《黑夜柔吠陀》《白夜柔吠陀》《娑摩吠陀》和《阿闼婆吠陀》,其中《黑夜柔吠陀》与《白夜柔吠陀》一般合称为《夜柔吠陀》。《梨俱吠陀》成书较早,约在公元前1500至前900年,故这一阶段被称为“早期吠陀时代”“梨俱吠陀时代”;《娑摩吠陀》《夜柔吠陀》《阿闼婆吠陀》三本成书于公元前900至前600年,其成书时代被称为“后吠陀时代”
《梨俱吠陀》是吠陀文学中、最古老、最重要的部分,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学,记载了雅利安人发展的轨迹,对印度宗教思想发展有重要研究意义。《梨俱吠陀》全书共十册,包含赞歌1028首。有一种观点认为除第一卷与第九卷,其余八卷是由同一个作者创作的作品组成,也可能是同一个家族的多个创作人使用同一个名字进行创作而成。这些赞歌的创作者被称为“仙人”,有名者共八位,多由师父口传于弟子,随后靠口口相传的方式一代代流传。《梨俱吠陀》的赞歌一部分为作为祭祀用的歌词和连祷文,也有部分是从祭祀仪式中独立出现的的文本“从此中可以感受到一种真正的原始宗教诗的气息”。
《夜柔吠陀》包括《黑夜柔吠陀》《白夜柔吠陀》两部分,其内容关于活祭。内容包含圣歌、散文词句(夜柔),其中一些散文具有韵律和诗意美,大多数赞歌也出自《梨俱吠陀》。
《娑摩吠陀》的内容关于神酒祭祀,现行译本共有1549首赞歌,除75首来自其他著作外其余的都可在《梨俱吠陀》中找到。

《阿闼婆吠陀》是四部吠陀中成书最晚的部分,其内容最吸引人。其现行译本共有731首赞歌,分为20册。其内容部分为《梨俱吠陀》翻译而来。
梵书又称净行书,即散文集,其内容为各种祭祀仪式和礼节的讲述。梵书反映了吠陀时代的精神,“那时全部的知识活动都集中于祭祀,它描述祭祀的礼节,讨论它的价值,推测它的起源和意义。”与《梨俱吠陀》相关的梵书有《爱达罗氏梵书》《海螺氏梵书》;与《娑摩吠陀》相关的梵书有《二十五大梵书》《耶摩尼梵书》;与《夜柔吠陀》相关的梵书有《鹧[zhè]鸪氏梵书》和《百道梵书》;与《阿闼婆吠陀》相关的梵书有《牛道梵书》等。
森林书又称阿兰若书,被认为是为退休至森林中的老年人创作的书籍。森林书也是组成梵书的一部分,如《爱达罗氏森林书》就是《爱达罗氏梵书》的续篇。
奥义书又称优波尼沙土,是教师私下授予学生的神秘训示论文,其内容驳杂,思想丰富,以唯心主义一元论和泛神论思想为主要观点。奥义书承认世界的灵魂梵天是最高存在;物质世界为虚幻的;灵魂能够轮回转世;只有与绝对存在物融为一体才能得到轮回解脱、安定,即“梵我一致”。奥义书一般为散文,部分也为韵文,现存的奥义书约一百余篇,包括《爱达罗氏奥义书》《布里哈德阿兰若奥义书》《海螺氏奥义书》《伊萨奥义书》《因孰奥义书》《灾厄奥义书》《普拉斯那奥义书》《孟达迦奥为书》《门多耶奥义书》《鹧鸪氏奥义书》《歌赞奥义书》《斯维特婆陀罗奥义书》等。
早期吠陀时代的宗教以自然崇拜为主,包括天空、阳光、空气、雨水、火等自然现象。根据赞歌记载,古仙人为政治崇拜某位特定神明,尚未发展成宗教,但吠陀时代是由单纯的自然崇拜发展至宗教的中间阶段,宗教诸神都起源于这一时期。在《梨俱吠陀》中记载了诸多神明,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单纯受人崇拜的上古神灵;仪式中受人敬拜的神;有着泛神论倾向的神。这一时期的雅利安人畏惧自然的威力、依靠自然的恩惠,故而将各种自然现象神化、人格化为神灵,通过简单的献祭和祈祷请求神灵消灾赐福。
婆罗门教形成于后吠陀时代,它在保留原始宗教多神崇拜的基础上,赋予了诸神新的内涵。例如,天神梵伦那演变为司法之神,雷电神因陀罗则成为国王和贵族的守护神。此外,婆罗门教还创造出大神婆罗摩,即大梵天,将其视为宇宙的创造者和最高主宰。
在理论构建上,婆罗门教对原始的万物有灵和灵魂转移观念进行了改造,提出了“业力轮回”的理论。这一理论认为,人的行动会产生后果,即业,而这些后果必将导致果报和轮回。婆罗门教的最高理想就是达到“梵我一致”的境界。

同时,婆罗门教也积极宣扬种姓制度,并为各个种姓规定了行为规范,即“法”(达磨)。只有遵循这些行为规范行动,人们才能获得善报。婆罗门的梵天神性说不仅概括了所有原始崇拜,更将其教义提升到了垄断精神世界的统治地位。因此,解释和宣传这一教义的婆罗门祭司僧侣也成为了社会阶级中最高的等级。
伐弹摩那·大雄被尊为耆那教的创始人,他大约生活在公元前6世纪的吠陀时代末期。大雄出生于北比哈尔的吠舍离镇附近的一个刹帝利部族,经过长期的苦修后,在四十二岁时达到了悟道的状态,从此被称为“耆那”(即情欲制胜者)或“尼犍多”(即从尘世的束缚中解脱),意味着他从尘世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他的门徒因此被称为耆那教徒或尼犍多。耆那教的核心教义包括反对吠陀经的权威和杀生祭祀,主张万物有灵、因果轮回,并强调苦修主义。在吠陀时代末期,耆那教与佛教形成了鲜明的对立,而当时孔雀王朝的月护王就是耆那教的信徒。
乔达摩是佛教的创始者,生卒年不详,但被认为是与耆那教创始者大雄同一时代的人;乔达摩是释迦族,出生于北方邦境内巴斯提县之北的尼泊尔低地,也属于刹帝利阶层。部分学者认为乔达摩“完全涅槃[pán]”于公元前483年或公元前543年,即后吠陀时代末期。乔达摩于三十五岁成佛(即觉者),其后一生致力于传道,将佛教传播至贝拿勒斯、奥德、比哈尔及其邻近地区等地。佛陀在吸收借鉴吠陀时代婆罗门教的教义后,对其进行批判和改进,从而诞生了佛教,主张四大庄严的真理:凡人都要受苦;苦必有因;苦必须解脱;为求解脱苦难,必须正道。但佛教不承认《吠陀经》的权威与吠陀仪式和祭祀的精神效果。
吠陀时代的饮食主要以奶油、蔬菜和水果为主。肉类食物可能仅用于大型宴会、家庭聚会,祭祀时会宰杀乳牛或阉牛款待宾客。饮酒也是吠陀时代社会中重要的饮食习惯,用谷类腌制的索摩(祭祀用酒)和空罗(普通酒)常在吠陀文学中被提及。
吠陀时代的娱乐活动在吠陀文学中有所记载,包括马车竞赛、掷骰[tóu]子、跳舞和音乐等。鼓、琵琶和横笛是吠陀时代常见的乐器。而大量的赞歌也说明在这一时期的音乐是很普及的娱乐活动。
吠陀时代妇女在婚姻选择方面具有一定的自由,一些女性可以选择自己所爱的男子结婚。当时,自选制度还未完全确立,但已开始萌芽,故需要父亲对女儿的自选进行监督。一些民间歌谣中也出现女性穿上美丽衣服与男子约会的情节。吠陀时代男女结婚时需要向婚姻之神毗婆薮祈福。结婚当日,父亲要将女儿献给苏摩、乾闼婆和阿格尼三位神明后,女儿才可出嫁;男子则要向阿厘耶门神发誓与妻子白头偕老、祈求造物主赐予其子嗣、向因陀罗神祈求幸福能够降临到妻子和子女身上。吠陀时代早期并没有一夫多妻制,直到后期才在赞歌中出现,国王和豪富阶级的人可广泛地实行一夫多妻制。另外,吠陀时代也允许寡妇再嫁。
吠陀时代的丧葬习俗有火葬和土葬,是区分人种的一种方式。原住民一般选择土葬,并树立石碑。而雅利安人则认为火葬是最为严肃的埋葬方法,他们相信死后火葬能够让灵魂从污秽的肉体中分离出来,获得第二次重生,继而进入第三生。火葬时,死者的亲友要环绕于死者四周,口中默念“眼睛归于太阳,呼吸化作风,四肢回归到来时的土、水、草、木中去。”吠陀时代的人们相信人去世后会前往祖先的国度即正义之国,与祖先相会,故而在生前就要相信、祭拜神明,以获得死后的幸福。

早期吠陀时代妇女地位很高,且没有过多束缚。因为这一时期妇女在社会经济结构中承担着农业、畜牧业、制造业等工作,且父系社会尚在形成时期。《梨俱吠陀》中记载,当时女性在社会上是受到尊重与敬仰的,可参加“毗达多”部落大会,并拥有一定参与政事的权利。教育对妇女是开放的,比没有妇女不许接受教育的规定;若一名女性能进行歌咏和作诗,则也可以担任女祭司主持宗教仪式;于是出现了如伽吉、梅特里伊等能够咏诵赞歌的女性。在宗教庆典、公共节日、娱乐活动中也没有任何禁忌。当时的宗教也不存在对女性必须结婚的约束,故也有女性可以选择不结婚而长留于父母身边。结了婚的女性则要负责家务和丈夫出门的需要。已婚妇女若正常接触社会则需要蒙面出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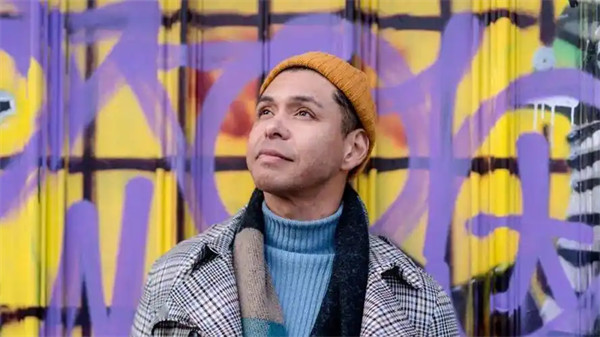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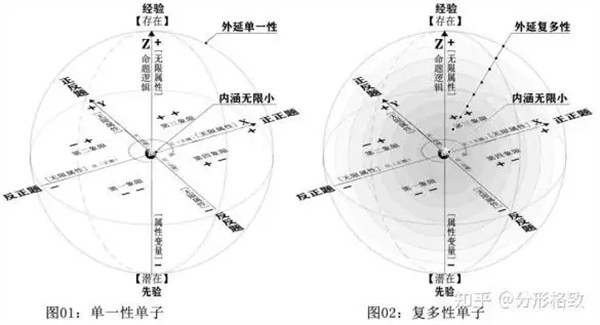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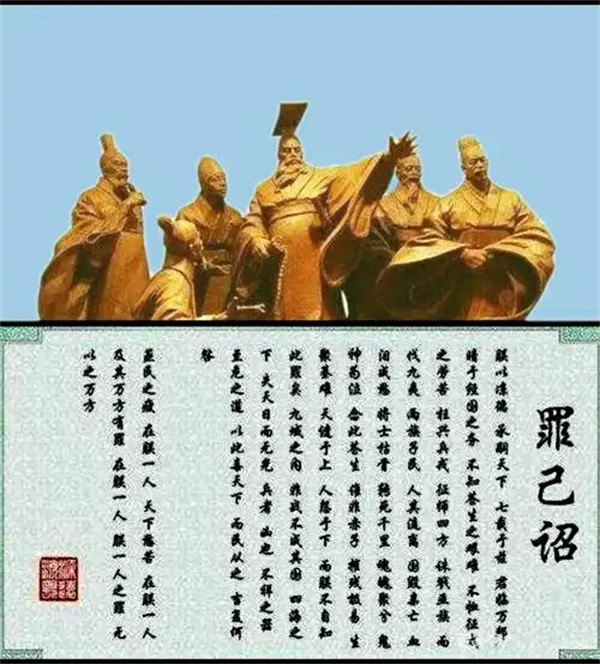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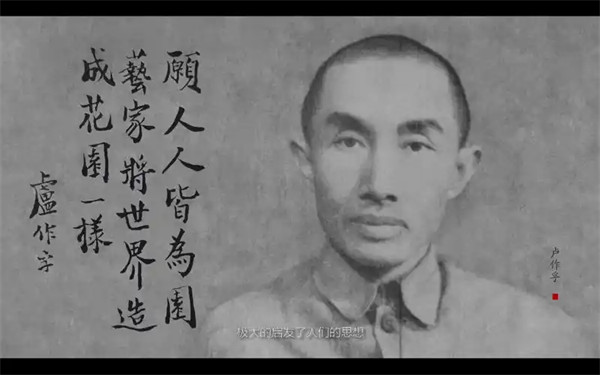







暂无评论内容